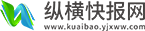世界短讯!财政压力大,不能只指望卖地!精简公职人员,“砸铁饭碗”势在必行
说实话,疫情虽然基本结束了,但今年的日子,仍然不好过。这两天网上讨论最多的就是外贸订单流失,港口空箱堆积如山,以及86年以上的连打螺丝都不配了。
当然,这俩说的是同一件事:订单不足,工厂不需要那么多人了。直观反映出今年的经济大环境依旧很恶劣。
另外,种种迹象表明,今年的就业压力也不容小觑,最典型的例子就是,上周末广西会展中心春招,一下涌进10万人找工作,据媒体报道,队伍都排到场馆外2公里了。
 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一边是1158万大学生毕业生面临找工作难,另一边却是财政供养人员突破8000万,仅财政供养费用就占税收比例超40%。
网上民怨沸腾,疫情三年,很多家庭收入锐减,自己勒紧裤腰带过活,竟然还要每7个人养一个公职人员。
事实上,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不仅仅是“供养焦虑”,还有真真切切的巨大财政压力。
2022年地方赤字创历史新高,站到了至高点5.9万亿,而2022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却减少2万亿,同比下滑23.3%。另外过去一年时间,商品房销售额减少了4.8万亿,各种和房地产相关的税收全部负增长。
一句话,过去二三十年,很多城市习以为常的“从土地里、房子里刨钱”的日子,已经开始撑不下去了。
房地产市场遇冷、土地财政后继乏力,就是很多城市面临的实打实的困难。
2月23日发生在河南商丘的公交停运“半日游”事件,根本原因还是财政补贴没到位。类似的情况,还有过年期间发生在黑龙江鹤岗宝泉岭的“暖气停供”事件,这说明在很多城市,地方财政问题已经开始影响公共服务了。
其实这两件事和城投暴雷的性质一样,就是背后的政府没钱了。因为这种涉及民生的暖气工程,都是在吃政府补贴。房地产不景气,卖地收入大幅下滑,地方开支却只增不减,很多城市入不敷出,地方政府不是魔术师,他变不出钱来。其结果只能是补贴跟不上,背后的企业支撑不下去。
知晓了其中的逻辑,我们再回过头来看,过去这一年多对房地产实施的强刺激,本质上还是地方想重走老路,想重启土地经济发展模式。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,根本带不动。
铁锤今天不是释放负能量,而是理性探讨解决之道。
我想说的是,财政压力大,不能只指望卖地。这并不是选择妥协的问题,而是压根就没得选的问题。
头部城市,尚可以依赖源源不断的需求,继续卖地,继续吃财政饭,但对于全国数以万计的中小城市而言,必须另辟蹊径。
根据这段时间,网上的消息发酵,大家应该也看懂了,专家给出的解决问题的出路有两个,一个是增加出生人口,一个是延迟退休。前者是刺激增量需求,后者是深挖存量需求。
在铁锤看来,这根本不现实。去年我国总人口首次负增长,一年时间,新生儿少了106万,看似减少不多,但其实已经走在下坡路上了,一方面,未来我国育龄妇女的数量,将保持每年减少400万-500万;另一方面,我国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,2020年已经接近10%。另外,影响生育的主要因素,是房子、医疗、教育这三座大山,短期看,这三座大山,都不可能卸除。换言之,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很难有实质性扭转。
在财政没钱的情况下,很多城市已经开始准备减肥瘦身,过紧日子——机构改革,精简公职人员,砸铁饭碗势在必行。
这是财政困境倒逼,使地方政府必须对现有行政体制动真格。
山西省、黑龙江省正在狂砸铁饭碗!
山西前后选择了两批共6个县城进行试点,对机构进行改革,对编制人员进行大幅精简。铁锤了解到,被选择的6个县有三个共同点:都是人口小县且都是人口流出型城市,都是产业工业匮乏县城,“保运转(工资、办公经费)、保民生”都严重依赖于财政转移支付。
直白点说就是,这些地方的财政真撑不住了。
从公布的结果来看,改革已初见成效:
河曲县,36个党政机构被精简到了22个,135名领导职数被精简为114名;186个涉改事业单位整合为40个,1964名事业编制被核减为659名,同时减少了75个科级职数。有903名事业人员超编。
石楼县,行政领导职数可精简18个,事业单位领导职数可精简9个,事业编制可精简178名。
娄烦县,9个县委机关减少至6个,26个政府部门降至16个,133个事业单位削减了29个。
根据河曲县委改革办介绍,超编人员朝一线下沉,级别高的当村(社区)两委主干,级别低的成为综治网格员,可能是非编。
黑龙江伊春、齐齐哈尔反向操作“撤街设镇”,其中伊春市动作最大,短短两个月时间就撤掉了六个街道办事处。
街道变镇,有什么影响?二者虽然是同级,但区别在于,一个是派出机构,一个是一级政府。派出机构能享受到各种配套优惠政策,一级政府福利要少得多。换言之,会带来辖区工业化、就业、财政收入、非农产业、公共服务及市政设施等方面的“缩水”和流失,因此势必会对部分公务员的岗位、级别等有“连锁冲击”。直白点说就是,财政供养人员要减少或者分流一部分。
精简之后,财政能省下来钱吗?答案是肯定的。
以山西省为例,这六个县市,改革后,单位运行成本平均降低5000余万元,人员经费平均减少2000余万元。尤其是河曲县,改革过渡期之后,县直部门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减少1050万元,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福利、“五险一金”等支出每年减少1.33亿元。
也就是说,一个县一年可以省下来7000余万的财政成本。山西省共有117个县市,全部照搬这个模式,一年至少为财政节余81亿元。
全国县市区合计2862个,大家可以计算一下,改革后能省下多少钱?更不要说财政开支占大头的城市了。
机构改革,首要目的是解决财政供养失衡和人浮于事问题。机构改革的最大阻力就是精减人员。缩编、减人,意味着一些人要下岗,这当然很难。
有人可能会说,下放到一线,仍然是财政在供养,换汤不换药。更重要的是,县里的编制腾出来了,以后还会继续招。精简来精简去,最后不减反增。增增减减,只不过是徒劳无功的改革罢了。
这话其实也没错了,机构改革的口号喊了几十年了,效果确实不怎么样,人数没减少,挪了个位置,还是财政在供养。
所以个人觉得,打破公职人员铁饭碗,最关键的有两个,一是取消隐性福利,二是要把虚职人员冗余的部门减下来。
正如前文所说,现在已经不是选择的问题,而是没得选的问题——很多地方的财政真撑不住了,到了必须折腾机关部门的地步了。
正如一位西部地区的县长所言:前几年土地好卖时,就愁钱花不出去,想办法花钱;现在土地卖不动了,就愁发不出钱,想办法找钱。
地方财政压力大,难以靠卖地生财,中央的转移支付有限,且不再对地方债务负责的大背景下,倒逼地方不得不对机构进行改革,裁撤冗余人员,降本增效。
国家机构、公职人员为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,谁也不能否认,也不会否认。经济形势不好,大家真的养不起那么多公职人员了,这也是很多地方必须正视的问题。
都知道上世纪90年代国企“下岗潮”对千千万万的家庭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,但造成这一结果发生的根本原因不能忽略,大批国有企业由于亏损严重、资不抵债,被裁撤、被并购。
我们今天很多城市所面临的问题,如出一辙,都是发展的问题。90年代的国企需要向新产业转型,适应大环境改变。现在的很多地方政府,同样如此,在完成了基建任务后,同样也要向经济体转型,即不能只指望卖地,你看这两年地卖不动了,问题就浮出水面了,有些地方没钱,连公交车都停运了。
-
世界短讯!财政压力大,不能只指望卖地!精简公职人员,“砸铁饭碗”势在必行
说实话,疫情虽然基本结束了,但今年的日子,仍然不好过。这两天网...
2023-02-28 -
环球观察:Z136/Z137次列车
1、Z136 137、Z138 135次列车是中国铁路运行于新疆首府乌鲁木齐至...
2023-02-28 -
全球微资讯!北方四季常开的花有哪些_北方四季常开的花
1、是在溫室裡種植的花 没有吧,只能说冬天盛开,那就有梅花!!有...
2023-02-28 -
全球快报:上线 24 小时卖出 200 万份,或许它才是今年的最大黑马?
在抢先体验版本上线后的24小时内,《森林之子》的销量就超过了200万...
2023-02-27 -
前沿热点:丁鼎
1、丁鼎,1985年生于江苏南通。2、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专职...
2023-02-27 -
天天热消息:指数刚好在范围,盘面乱轮熬不应期,炒王字辈,如何判断板块是否主流?
【如何判断板块在主流】题材炒作当板块爆发的时候,大家应该第一时...
2023-02-27 -
今日热门!西安公租房申请进度怎么查
一、西安保障性住房平台查询1、进入西安保障性住房平台2、选择案件...
2023-02-27 -
每日热文:5号线北延伸段今日通车,中央公园再添重要轨道大动脉!
期待已久的轨道5号线延伸段,今日迎来正式通车。“以后坐轻轨,从中...
2023-02-27 -
环球实时:iphone照片快速导入电脑_苹果手机照片如何导入电脑
1、方法 步骤1 将苹果手机数据线连在电脑上,在我的电脑里面打开...
2023-02-27 -
世界滚动:上海:将在“大零号湾”内推进细胞疗法、基因疗法、脑机接口等技术研发和应用
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官网2023年2月27日消息,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等部...
2023-02-27 -
环球速读:蔚来为什么会亏损到这种地步!
蔚来为什么会亏损到这种地步!,李斌,电池,酸辣粉,商用车,电动车,绿色...
2023-02-27 -
天天即时:美元二次冲顶人民币“破7”在即:据一财,年初华尔街“看跌美元”的一致共识快速反转,美元指数从101反弹至105,人民币对美元则从6.7再度跌至7附近。一方面,通胀和就业数据支持美元“二次冲顶”
美元二次冲顶人民币“破7”在即:据一财,年初华尔街“看跌美元”的...
2023-02-27 -
环球快讯:上海房地产发展报告_2015-2016
1、《上海房地产发展报告(2015-2016)》是201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...
2023-02-27 -
视焦点讯!麻仁丸的功效与作用及有副作用_麻仁丸的功效与作用及有副作用吗
1、马人润肠丸是消化内科的常用药,主要用于暂时性通便治疗。2、马...
2023-02-27 -
今日最新!沙僧的武器_说一说沙僧的武器的简介
夏弥来为大家解答以下的问题,沙僧的武器,说一说沙僧的武器的简介...
2023-02-27 -
天天热讯:不可用性
1、不可用性(unavailability)是指在给定的瞬时或在给定的时间间隔...
2023-02-27 -
【天天报资讯】皮埃尔·布莱斯
1、皮埃尔·布莱斯,演员,参演电影《达契亚人》《第7号天堂》《死...
2023-02-27 -
焦点滚动:灰蝗虫的婚恋_灰蝗虫
1、灰蝗虫的习性:成虫与蝗蝻的食性相同,均为植食性,而且成虫期补...
2023-02-26 -
热点!辛香汇
1、辛香汇,原名厚味香辣馆,创始于2003年,起源于上海,是一家性价...
2023-02-26 -
快资讯:documentary-documentary是什么意思
1、documentary[7dCkju5mentEri]n 记录片adj 文件的纪录片记录片,...
2023-02-26 -
【全球播资讯】阿圭罗:梅西正认真考虑为纽维尔老男孩踢球,球迷:球王情怀
因为梅西尚没与巴黎续约,关于梅西的下家,一直是球迷关注的话题。...
2023-02-26 -
【天天新要闻】山柳菊
1、山柳菊(学名:HieraciumumbellatumL ),是多年生草本植物,高...
2023-02-26 -
全球消息!NBA3X全国总决赛广州开幕,各大“网红”球员同场竞技
NBA3X全国总决赛广州开幕,各大“网红”球员同场竞技
2023-02-26 -
每日快讯!163个科技成果亮相 国家科技计划成果路演行动首次在线下进行
2月25日,国家科技计划成果路演行动——武汉东湖高新区专场路演活动...
2023-02-26 -
全球观焦点:补习学校
1、补习学校(Fortbidungsschule),亦称“继续学校”。2、德国具有...
2023-02-26 -
观热点:比亚迪王朝小兄弟,脸庞随“汉”,价格数字浪漫却发飘
比亚迪王朝小兄弟,脸庞随“汉”,价格数字浪漫却发飘如果把时间退...
2023-02-26 -
【天天新视野】中国当代花鸟画大家邢少臣
1、《中国当代花鸟画大家邢少臣》是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图书。...
2023-02-25 -
焦点讯息:皮下埋植剂植入避孕术
1、皮下埋植剂植入避孕术是一种新型的避孕方法,目前已在全世界推广...
2023-02-25 -
焦点资讯:39万余人赴考 2023河南省考结束
2月25日16时30分,随着哨声的响起,2023年河南公务员笔试正式结束。...
2023-02-25 -
焦点速读:二泉
1、刘二泉是《一代枭雄》里面的人物。2、刘庆福的二女儿,何辅堂妻...
2023-02-25